我铺开马衣,躺在峡谷边上;周围——一堆堆新割的草垛,清香扑鼻,让你懒懒地直发困。机灵的主人们把禾草摊开在屋前:晒得干透些,好收进草棚子去!要是能在这上面睡它一觉,那该有多好!
孩子们鬈发蓬松的小脑袋,从一个个草堆里冒出来;带凤头的母鸡在干草里寻觅着蚊蚋和虫豸;蓬乱的草茎中一只白唇的小狗在打滚。
几个长着亚麻色鬈发的小伙子,身穿束着低低腰带的干净衬衫,脚登镶边的厚实长统靴,他们把胸脯靠在卸了马的大车上,正伶牙俐齿地相互抢嘴说笑。
窗口探出一张年轻女人的圆圆的脸来;她在笑着,不知是笑他们的嚼舌,还是在笑乱草堆里孩子们的嬉闹。
另一个年轻女人用一双有劲的手从井里提上一只湿淋淋的大吊桶……吊桶在抖动,在绳端摇荡,晃出了一串串发亮的水滴。
我面前站着一个老农妇,她是女主人,穿着格子呢的新裙子和一双新皮靴。
她那黑瘦的脖子上挂着绕了三圈的大串珠;白发上裹着一块黄底红点子的头巾,低垂在她混浊的眼睛上。
然而这双老眼在温和地微笑;整张皱纹密布的脸都在微笑。想必,老大娘该有七十了……不过,就是现在也还看得出:她当年可是个美人儿呢!
她那晒得黑黑的右手手指张开着,端了一瓦钵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没撇过奶油的冷牛奶;瓦钵外边还蒙着一层珍珠似的水珠子。老大娘左手托着一大块还有点温热的面包递给我。
“吃吧,”她说,“请随意,过往的客人!”
孩子们鬈发蓬松的小脑袋,从一个个草堆里冒出来;带凤头的母鸡在干草里寻觅着蚊蚋和虫豸;蓬乱的草茎中一只白唇的小狗在打滚。
几个长着亚麻色鬈发的小伙子,身穿束着低低腰带的干净衬衫,脚登镶边的厚实长统靴,他们把胸脯靠在卸了马的大车上,正伶牙俐齿地相互抢嘴说笑。
窗口探出一张年轻女人的圆圆的脸来;她在笑着,不知是笑他们的嚼舌,还是在笑乱草堆里孩子们的嬉闹。
另一个年轻女人用一双有劲的手从井里提上一只湿淋淋的大吊桶……吊桶在抖动,在绳端摇荡,晃出了一串串发亮的水滴。
我面前站着一个老农妇,她是女主人,穿着格子呢的新裙子和一双新皮靴。
她那黑瘦的脖子上挂着绕了三圈的大串珠;白发上裹着一块黄底红点子的头巾,低垂在她混浊的眼睛上。
然而这双老眼在温和地微笑;整张皱纹密布的脸都在微笑。想必,老大娘该有七十了……不过,就是现在也还看得出:她当年可是个美人儿呢!
她那晒得黑黑的右手手指张开着,端了一瓦钵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没撇过奶油的冷牛奶;瓦钵外边还蒙着一层珍珠似的水珠子。老大娘左手托着一大块还有点温热的面包递给我。
“吃吧,”她说,“请随意,过往的客人!”
伤感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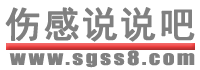
 上一篇:想骂一个背叛者经典句子
上一篇:想骂一个背叛者经典句子 下一篇:背叛的配图
下一篇:背叛的配图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