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我立即就记下这个菜谱,其主要成分是自我克制。不过,诗歌句子总有一个癖好,就是会偏离上下文,跑进了普遍意义,因此,每当我开始在纸上写点什么的时候,“会既不走也不送他儿子”所包含的吓人的荒诞感就会开始在我的下意识里回荡。
我想,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谓的影响,除了那种荒诞感不是诗人的发明而是现实的反映;发明是很少看得出来的。我可在这行诗中受益于这位诗人的,不是其情绪本身而是其处理方式:安静,不强调,没有任何踏板,几乎是信手拈来。这种处理手法之所以对我特别重要,恰恰是因为我是在60年代初遇到这行诗的,“荒诞派戏剧”正大行其道。
在这个背景下,奥登对题材的处理尤其瞩目,不仅因为他领先很多人,而且因为他诗中包含颇为不同的伦理信息。至少对我来说,他对这行诗的处理手法是很有力的:有点像“别喊狼来了”,尽管狼就在门口。(我想加上一句:即使那匹狼酷似你。正因为这样,就更别喊狼来了。)
虽然对一个作家来说,提及自己的刑事经验——或就此而言,任何艰苦经验——就如同正常人提及名人以自抬身价,但很碰巧,我下一次较仔细地看奥登,发生于我在北方服刑期间,那是一个小村子,隐没在沼泽和森林中,靠近北极。这一回,我手头的选集,是莫斯科朋友寄来的一本英语诗选。它收录了很多叶芝的诗,当时我觉得叶芝太重修辞,
我想,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谓的影响,除了那种荒诞感不是诗人的发明而是现实的反映;发明是很少看得出来的。我可在这行诗中受益于这位诗人的,不是其情绪本身而是其处理方式:安静,不强调,没有任何踏板,几乎是信手拈来。这种处理手法之所以对我特别重要,恰恰是因为我是在60年代初遇到这行诗的,“荒诞派戏剧”正大行其道。

在这个背景下,奥登对题材的处理尤其瞩目,不仅因为他领先很多人,而且因为他诗中包含颇为不同的伦理信息。至少对我来说,他对这行诗的处理手法是很有力的:有点像“别喊狼来了”,尽管狼就在门口。(我想加上一句:即使那匹狼酷似你。正因为这样,就更别喊狼来了。)
虽然对一个作家来说,提及自己的刑事经验——或就此而言,任何艰苦经验——就如同正常人提及名人以自抬身价,但很碰巧,我下一次较仔细地看奥登,发生于我在北方服刑期间,那是一个小村子,隐没在沼泽和森林中,靠近北极。这一回,我手头的选集,是莫斯科朋友寄来的一本英语诗选。它收录了很多叶芝的诗,当时我觉得叶芝太重修辞,
伤感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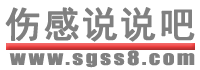
 上一篇:想骂一个背叛者经典句子
上一篇:想骂一个背叛者经典句子 下一篇:背叛的配图
下一篇:背叛的配图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