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男孩再一次尖声哭叫……我本想拉住个同伴,可是,我们都被墨水样黑糊糊、冰冷的、怒吼着的浪涛压倒了、埋葬了、淹没了、冲走了!
黑暗……无尽期的黑暗!
我几乎透不过气来,于是醒了。
1878年3月
玛莎
多年前——我住在彼得堡,每次雇了街头马车,总要跟车夫闲聊几句。
我特别喜欢跟夜间赶车的车夫聊天儿,他们都是近郊的贫苦农民,驾着涂成赭石色的小雪橇和瘦弱的驽马来到京城——期望能糊个口,能凑些钱回去向老爷交租。
有一回,我雇的一个车夫……一个二十来岁、身材高大匀称的帅小伙;他眼睛碧蓝,面颊红润;一顶打着补丁的小帽低压在眉上,下面露出一卷卷亚麻色的头发。而他身上那件开了裂的粗呢外衣,也只能勉强遮住他魁梧的肩膀!
可是,马车夫那张漂亮的、没长胡子的脸似乎现出了哀愁与忧郁。
我与他攀谈起来。他的声音含着悲伤。
“怎么啦,兄弟?”我问他,“你怎么不快活?莫非有什么伤心事吧?”
小伙子没有立即回答。
“是呀,老爷,是呀,”他终于说了起来。“是这么回事,再没有更不得了的大事了。我的老婆死了。”
“你爱她……你的老婆?”
黑暗……无尽期的黑暗!
我几乎透不过气来,于是醒了。
1878年3月
玛莎
多年前——我住在彼得堡,每次雇了街头马车,总要跟车夫闲聊几句。
我特别喜欢跟夜间赶车的车夫聊天儿,他们都是近郊的贫苦农民,驾着涂成赭石色的小雪橇和瘦弱的驽马来到京城——期望能糊个口,能凑些钱回去向老爷交租。
有一回,我雇的一个车夫……一个二十来岁、身材高大匀称的帅小伙;他眼睛碧蓝,面颊红润;一顶打着补丁的小帽低压在眉上,下面露出一卷卷亚麻色的头发。而他身上那件开了裂的粗呢外衣,也只能勉强遮住他魁梧的肩膀!
可是,马车夫那张漂亮的、没长胡子的脸似乎现出了哀愁与忧郁。
我与他攀谈起来。他的声音含着悲伤。
“怎么啦,兄弟?”我问他,“你怎么不快活?莫非有什么伤心事吧?”

小伙子没有立即回答。
“是呀,老爷,是呀,”他终于说了起来。“是这么回事,再没有更不得了的大事了。我的老婆死了。”
“你爱她……你的老婆?”
伤感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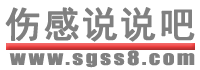
 上一篇:想骂一个背叛者经典句子
上一篇:想骂一个背叛者经典句子 下一篇:背叛的配图
下一篇:背叛的配图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