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这位同桌头一次听见我这么诚恳的说话,一时间没有适应过来,微微一笑,说:“不过说实话,你的声音很好听,尤其是学校的歌唱大赛。你喜欢任贤齐吗,你挺适合唱他的歌。”
那位男生插过话来,说:“你还别说,刘稀玉的歌唱得真不错,把那个谁,哦,张露露给迷的,哈哈...”
“哇哦…”旁边的人听到这个话题,又开始冲我嬉笑起哄。
我和张露露的事情,是全校的公开知名事件,我有时候就在想,即便是我和张露露真的谈恋爱了,这么众目睽睽之下,这帮人这么起哄,也什么都干不了。
“行啦,人家都走了,什么事情都没有!”我说。
“那你不伤心死了?”那个男生继续逗我。
我正想辩驳,我差一点就喊出来,“我正在和杨老师谈恋爱”,瞬间将这句话狠狠地咽到肚子了,我的心脏快速紧张的跳动,想想都后怕。
我忽然间意识到,我和杨老师开始的这段感情,必须一直深埋地下,不能见光,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,我不敢想象如果大伙儿知道了,我该如何面对?更加难以想象的是,杨老师该如何面对?我差一点就闯了弥天大祸,万劫不复。
周六我一早就醒了,我洗了个澡,穿上一件我认为最好看的衣服,然后不停地照镜子,摆弄着我的头发。
十六七岁的少年情窦初开,就像初次绽放的花朵,伴随着初生的朝阳,招蜂引蝶,享受着免费的阳光,与自然万物的赞美声。慢慢地,随着年龄的增长,自以为成熟的心听从了世俗的建议,更加看重果实,岂不知摘下果实那一刻伴随着的将是永恒地枯萎凋零。
人活着只有一个结果,就是从出生到死亡,那些花儿绽放的时节,称之为青春。
我忐忑又兴奋的来到了图书大厦。
我远远地看见了杨老师,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,双手搭在栏杆上,一阵阵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,裙角飞扬,满怀心事地望着马路上的车流,等待着我。
我兴奋,紧张,激动,又怀着一丝丝的罪恶感,常年义务教育形成的价值观让我感到相当荒谬,我竟然和我的老师约会,她是我的长辈,是传授我知识的人,“天地君亲师”,脑子里一连串的大道理在回响。
那位男生插过话来,说:“你还别说,刘稀玉的歌唱得真不错,把那个谁,哦,张露露给迷的,哈哈...”
“哇哦…”旁边的人听到这个话题,又开始冲我嬉笑起哄。
我和张露露的事情,是全校的公开知名事件,我有时候就在想,即便是我和张露露真的谈恋爱了,这么众目睽睽之下,这帮人这么起哄,也什么都干不了。
“行啦,人家都走了,什么事情都没有!”我说。
“那你不伤心死了?”那个男生继续逗我。
我正想辩驳,我差一点就喊出来,“我正在和杨老师谈恋爱”,瞬间将这句话狠狠地咽到肚子了,我的心脏快速紧张的跳动,想想都后怕。
我忽然间意识到,我和杨老师开始的这段感情,必须一直深埋地下,不能见光,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,我不敢想象如果大伙儿知道了,我该如何面对?更加难以想象的是,杨老师该如何面对?我差一点就闯了弥天大祸,万劫不复。
周六我一早就醒了,我洗了个澡,穿上一件我认为最好看的衣服,然后不停地照镜子,摆弄着我的头发。
十六七岁的少年情窦初开,就像初次绽放的花朵,伴随着初生的朝阳,招蜂引蝶,享受着免费的阳光,与自然万物的赞美声。慢慢地,随着年龄的增长,自以为成熟的心听从了世俗的建议,更加看重果实,岂不知摘下果实那一刻伴随着的将是永恒地枯萎凋零。
人活着只有一个结果,就是从出生到死亡,那些花儿绽放的时节,称之为青春。
我忐忑又兴奋的来到了图书大厦。
我远远地看见了杨老师,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,双手搭在栏杆上,一阵阵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,裙角飞扬,满怀心事地望着马路上的车流,等待着我。
我兴奋,紧张,激动,又怀着一丝丝的罪恶感,常年义务教育形成的价值观让我感到相当荒谬,我竟然和我的老师约会,她是我的长辈,是传授我知识的人,“天地君亲师”,脑子里一连串的大道理在回响。
伤感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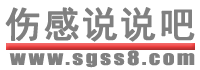
 上一篇: 公婬荡乱婬小说纯肉 荡公乱妇rss
上一篇: 公婬荡乱婬小说纯肉 荡公乱妇rss 下一篇:第一章张敏陈红陈法蓉 老汉扛起娇妻玉腿进入
下一篇:第一章张敏陈红陈法蓉 老汉扛起娇妻玉腿进入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