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烧肉是爸爸的拿手菜,堪称“一绝”。
通常周六,爸爸早早地上街买了上好的五花肉,肥瘦适中的一大块,然后一个上午都泡在厨房里。
先将肉洗净,放在切板上,手起刀落,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,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。
紧接着,点上煤气,坐上铁锅,倒进油,趁等油热的当儿,切几片薄薄的生姜,放进锅里。锅热了,油也热了,我的心也被烘热了。
等油锅里不断鼓起一个又一个透明的泡泡时,爸爸端起切好的五花肉,沿着锅边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麻利倒下,油锅里顿时像大年放鞭炮一样“噼里啪啦”炸响了,爸爸操起铲子,左一下右一下,不停地翻炒着。白面书生一样的肉皮在渐渐平息的爆炸声中,变了颜色,肉块儿不经意间缩小了一圈,像练了无敌缩骨功,变得短小精悍。
炒出了油后,倒入料酒,老抽,放入几粒冰糖,加水漫过肉,盖上锅盖,大火烧开,小火慢炖。爸爸的动作行云流水般熟练,不慌不忙,又富含节奏。渐渐地,肉的表面像涂了蜡一样红且亮。他紧盯着锅,查看火候,那专注的神情,像顶尖的工匠,凝视着自己精心打磨即将完工的作品一样。
锅里,肉被深红色的汤汁浸泡着、拥抱着,在小火中细熬,“咕嘟”“咕嘟”,大大小小的泡泡欢快地此起彼伏。一种奇异的香味随着烟雾袅袅升起,像细细的线,钻进我的鼻子,顺着喉咙一路向下,密密缠绕着五脏六腑。
通常周六,爸爸早早地上街买了上好的五花肉,肥瘦适中的一大块,然后一个上午都泡在厨房里。
先将肉洗净,放在切板上,手起刀落,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,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。
紧接着,点上煤气,坐上铁锅,倒进油,趁等油热的当儿,切几片薄薄的生姜,放进锅里。锅热了,油也热了,我的心也被烘热了。
等油锅里不断鼓起一个又一个透明的泡泡时,爸爸端起切好的五花肉,沿着锅边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麻利倒下,油锅里顿时像大年放鞭炮一样“噼里啪啦”炸响了,爸爸操起铲子,左一下右一下,不停地翻炒着。白面书生一样的肉皮在渐渐平息的爆炸声中,变了颜色,肉块儿不经意间缩小了一圈,像练了无敌缩骨功,变得短小精悍。

炒出了油后,倒入料酒,老抽,放入几粒冰糖,加水漫过肉,盖上锅盖,大火烧开,小火慢炖。爸爸的动作行云流水般熟练,不慌不忙,又富含节奏。渐渐地,肉的表面像涂了蜡一样红且亮。他紧盯着锅,查看火候,那专注的神情,像顶尖的工匠,凝视着自己精心打磨即将完工的作品一样。
锅里,肉被深红色的汤汁浸泡着、拥抱着,在小火中细熬,“咕嘟”“咕嘟”,大大小小的泡泡欢快地此起彼伏。一种奇异的香味随着烟雾袅袅升起,像细细的线,钻进我的鼻子,顺着喉咙一路向下,密密缠绕着五脏六腑。
伤感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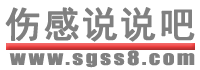
 上一篇:爸爸的胬肉 帮爸爸传宗接代
上一篇:爸爸的胬肉 帮爸爸传宗接代 下一篇: 妈妈爷爷你们在干嘛 故意让爸爸看到
下一篇: 妈妈爷爷你们在干嘛 故意让爸爸看到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