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飘泊的大雨不停不停地下,客栈里来来往往的人无不抱怨着天气的恶劣,可倒是乐坏了掌柜的嘴脸,小二这一端刚摆好菜,那一端又叫嚷着汤水。脾气大些的粗汉大口吞下一西瓜的果肉,随手丢在客栈门外的尘土中,一拍啤酒肚,粗声道:“就这屁点儿大的雨还怕?算啥好汉?”一句话不免惹人嘲弄,那粗汉火气上来,一把拎起那富商子弟,
抬手就要盖一巴掌,骂道:“你奶奶的算个屁!砸钱也混不进姑苏去,连云梦那江家也不收你,呵,还想修仙,你他娘的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!”平民百姓家的,哪一个不想攀个修仙世家,老底就这么被挖出来,那富商子弟脸色沉沉的不免感到难堪,怒骂道:“你这就会杀猪的屠夫懂个什么?你借了我家多少钱了?你他妈是不想混了是吧?
”这两人正缠斗着,四座的人无不看戏、评论、唏嘘,也有想要趁机高攀上去搭把手的,最终还是让几个跑堂拉开来,那粗汉碰了一鼻子灰,淋着雨出了店门,那富商子弟坐下也没了胃口,夹了些菜,一摔筷子便离开了,余人虽三三两两地重又聊起来,但未免拘谨,瞅着雨势渐小,稀稀疏疏地也都离开了。
客栈也赚足了钱财,掌柜打了个哈欠,大摇大摆地关上了店门,木门雕刻着兰陵金氏的金星雪浪纹,冷风一吹,纵使是富贵的牡丹,也不免有些冷清。街上再没什么人了,客栈旁漆黑的小巷蹑手蹑脚地出来一位四五岁大的孩童,探出头来,一双炯亮的眼小心翼翼地探查着四周,确认了没有他的“死对头”后,他拔腿飞跑向客栈旁的垃圾堆,
冻得发红的手在垃圾间仔细翻找,又抬起头焦虑地四处张望,无意中却倒是瞥见了另一头的西瓜皮,顿时眼底的星辰都被点亮了,屁颠屁颠地跑向那块沾满尘土与唾沫的西瓜皮。 身后是野狗凶恶的狂吠,他还没有防备,就被尖利的二十几颗利牙狠狠咬住肩头,那力道简直像是要将他的血肉撕下一般,
伤感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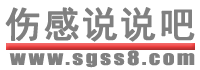
 上一篇:蘅羡rroooollllll【all羡】
上一篇:蘅羡rroooollllll【all羡】 下一篇:温若寒玩蓝湛蓝涣 ★私设有,ooc严重
下一篇:温若寒玩蓝湛蓝涣 ★私设有,ooc严重






